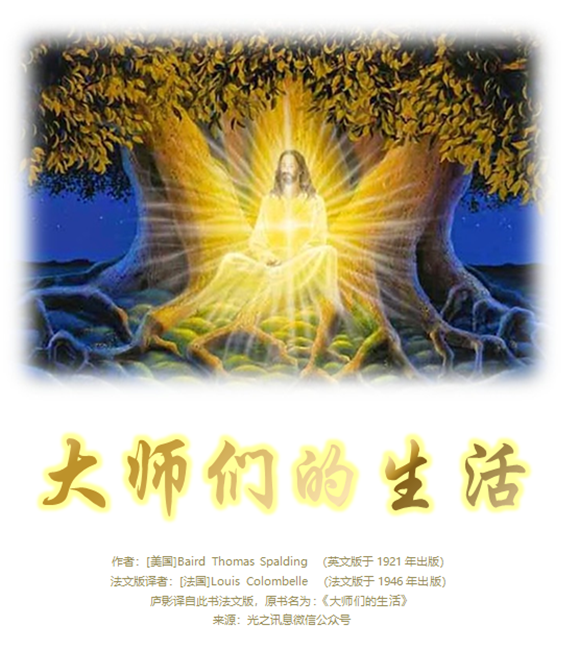
暴风雪中的上帝之家
从这时起,我们在钱德·森指导下专心致志、努力认真地学习字母表。时光飞逝而去,快得令人目眩。到四月底,我们出发前往戈壁沙漠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而大部分文献还没有翻译出来。我们心想将来还可以再回来完成这项工作,以此来宽慰自己。大师朋友们已经替我们翻译了很多文献,但他们坚持让我们学习那些文字,一定要让我们能够自己翻译。
去年九月,我们商定在戈壁沙漠中与考察队的其他成员会面,然后他们将陪我们一起去那有可能是三座古城遗址的地方。某些文献给出了那三座古城的准确位置。我们还没看到那些文献,但听人说起过。我们手头只有一些抄本,而它们已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这两套文献使那些城市的繁盛时期可以追溯到二十多万年前。它们的居民似乎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了解艺术和工艺,加工过铁和黄金。这后一种金属在当时十分常见,以至于人们用它来制造餐具和钉马掌。据说那些人能完全掌控各种自然力,也能完全掌控他们自身那来自于上帝的能力。实际上,这些传说(假如是传说的话)与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出奇地相似。
如果相关地图是准确的,那么维吾尔大帝国当时覆盖着亚洲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欧洲,直到今天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它的最高海拔高度是海平面以上两百米。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广阔平原,非常富饶,人口众多,是母大陆的一块移民地。假如发现其城市的遗迹,那对历史学无疑将是十分重大的贡献。从对七王王朝的描写来看,这个国家当时的繁盛与辉煌远远超过了古埃及。
根据那些粘土板的描述,这个地区甚至在七王时代之前就已经比埃及繁荣、发达得多。人们在那里实行自治,因此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诸侯或奴隶。最高首领被称作“指导本源”。这是确定无疑的。粘土板上明确记载说他的住所就在民众中间,人民热爱他并服从他。粘土板上还记载说: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从指导本源那里篡夺了统治权以使自己登上宝座并发号施令。
时间继续快速流逝,而我们为准备考察队的出发而分外忙碌。我们得在五月到达一个约好的地点。我们打算在那里补充食物和装备,以便完成最后的旅程。
当定好的出发日期临近时,我的想法和感觉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待在这里的每一个小时都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我们已经和这些人一起待了五个多月,而且在此期间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但还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快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几个月就像才过了几天一样。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仿佛有一扇通往无限可能性的门大大地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曾觉得只要跨过这扇门就行,但我们犹豫不定,正如我们犹豫着、舍不得离开这些被我们视为兄弟的神奇人物一般。
我想每个世俗之人一生中都会有那么一刻看到门户大开,就像我们在那个美好的四月天看到自己能够达到的种种无限可能性一样。我请读者暂时抛开一切成见,尽可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我并不是要读者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我是想让读者明白,描述大师们的生活和坐在他们脚边听他们讲话是不同的。似乎我们只要愿意勇敢地走上前去、跨过那扇门,就会变成圆满成就的大师。然而我们犹豫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彻底。我们听任那些习惯性的想法把自己往后拽并关上了那扇门。事后我们说那扇门是被命运关上的,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命运就取决于我们自己。
再看看这些亲切、单纯而又神奇的人吧。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许多生世中跨过了那扇门,也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跨过去的。他们过着灵性生活。他们不恪守先例或传统,只是过着一种纯净、正直的生活,过得扎扎实实、脚踏实地。我请读者自己去进行比较吧。我们舍不得离开这些亲爱的灵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然而我们也如饥似渴地望着未来,知道还有其它体验在等着我们。
终于,在这个灿烂的四月天,我们告别了大师朋友们。他们真诚地握住我们的手,衷心邀请我们日后再来。我们最后一次向他们道了别,然后转向北方,去穿越戈壁大漠。此地流传的一些可怕的历险故事如同阴暗的幻影般令我们浮想联翩。但是我们没有害怕,因为埃弥尔和贾斯特再次与我们同行,而钱德·森取代了尼普鲁。我们其他人也都是旅行老手了,走在沙漠旅队的艰难路途上对我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我确信我们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很高兴来到这里。所有人都认识到:一个新世界已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地区有多么偏僻,也都知道以惯常的方式做这种旅行要冒怎样的风险。然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我们前行。对大师朋友们的绝对信任使我们把一切替自己担忧、畏难的想法都抛到了风中。我们以一种学生般的狂热激情投入到冒险之中。
我们曾多次见识过大地上一些极其偏僻的地方,但从未到过如此遥远、荒僻之处。然而我们能无比自在、轻松地在这里旅行。我们对这个地方以及对我们恩人们的这种迷恋,应该不会令读者感到吃惊。我们一度觉得可以一直向北越过极地并征服那些地区。还没走出多远我们中的一人就说:“哦!可惜咱们不能像大师朋友们那样旅行,否则这旅程会是多么轻松啊!就因为咱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才迫使他们也得和咱们一起费劲儿地走路。”
直到第九天傍晚,一切都很顺利。这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时,我们刚从一条深深的溪谷中走出来——沿着那条溪谷走是为了到达下游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区。这时考察队的一名成员让大家注意远处的一些骑手。我们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发现共有二十七名似乎武装到了牙齿的骑手。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贾斯特。他回答说那可能是侵扰这个地区的流浪团伙之一。我们问这是不是一伙强盗。他回答说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畜群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离开旅道,走向一个树丛,在那儿扎下营来好过夜。当大家扎营时,我们中的两人穿过营地旁的激流,登上了一座山脊。从那里可以看到我们发现那伙骑手时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两个人到山顶上后站住了,用望远镜看了看,然后急忙返回了营地。一走到足够近的距离,他们便大声喊着说:那伙骑手离我们不到五十公里远了,正在向我们这儿行进。
就在这时,有人注意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们仔细看了看天空,果然看到厚重的云团在西北方聚集起来,雾气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靠近。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伙骑手直朝着我们的营地冲下来。虽然我们有三十二个人,却没有一件火器。这让我们很慌乱。
很快我们便遭到了风暴的猛烈打击。这让我们更加恐惧,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风暴在这些荒僻山区有多么狂暴、凶猛。风速一度达到了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夹杂着小冰粒抽打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周围咆哮、怒吼。我们恐怕不得不换个地方宿营,以免被折断的树枝砸到。随后我们所在之处的空气平静了下来。我们一度以为这场风暴只是暂时性的,就像这个地区常有的那种突然来袭的暴风雨一样。
半明半暗中我们能看清楚一些了,于是忙着收拾各个帐篷里的东西。这花了我们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刚才还让我们那么忧心的风暴和强盗,现在全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把手里的活儿停下了一会儿。我们队长走向帐篷口,往外看了看,转回身说道:“附近的风暴好像很猛烈,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微风。你们看,这帐篷和我们周围的树木几乎都没有摇动。空气又暖和又清香。”
我们许多人跟着他去了外面,一时都陷入了惊讶之中。我们刚才整理帐篷内部时,对风暴只有模糊的意识。我们以为它已经从这里过去,沿着溪谷往上走了。某些大气扰动确实会如旋风般穿过这个地区。它们在几公里范围内肆虐,然后平息下来,接着天气往往会很平静。可这次却不是这种情况。暴风在我们三十米外刮着,我们近旁的空气却平静而又暖和。然而我们以前在类似的风暴中观察到的是:会有一股强烈的寒冷把人穿透。人几乎会在那风中窒息,因为那狂风会胡乱把针尖般扎人的冰粒刮到人脸上。
突然,我们这块平静的区域像施了魔法般被照亮了。我们在惊愕中似乎听到狂风呼啸里传出人的喊叫声。这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开饭了。我们进入帐篷坐下来。吃饭时,我们中有一个人担心那些刚才冲下山坡的骑手会遇到麻烦。另一个人说道:“我们在外面时好像听到了喊叫声。要是那些骑手在风暴中迷了路,我们难道不能提供救援吗?”
贾斯特开口讲话了。他说那些人属于这附近地区最出名的强盗团伙之一。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整天对那些村庄进行偷盗和抢掠,还夺走成群的山羊与绵羊。
晚饭后,当风暴暂时平息时,我们听到了喊叫声以及马的嘶叫声和鼻子喷气声,似乎它们的骑手已经控制不住它们了。这些声音仿佛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的,但由于旋转的风雪过于浓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点营火的亮光。
很快埃弥尔站了起来,说他要去邀请那些强盗来我们的营地,因为在这场风暴中除非是万幸,否则没有一个人或一只动物能活到早晨。
外面的确已经变得更加寒冷了。我们中的两个人请求陪埃弥尔一起去。这似乎让他很高兴。他同意了,于是他们三个便都消失在风暴中。二十多分钟后,他们又出现了,后面跟着二十个牵着马缰绳的强盗。这些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七个人和团伙失去了联系,可能在风暴中迷了路。
这群强盗是一伙半野蛮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进入到有亮光的圈子里后,他们似乎怀疑我们设下了圈套想捉住他们。看得出他们很惊恐,但埃弥尔向他们保证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地离开。他告诉他们说:假如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卫的。他们的头领承认:当他们在风暴前看见我们从溪谷里出来时,确实是想攻击我们来着。可后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因为他们深深地迷了路,都找不到自己营地的方向了。当埃弥尔和我们的两个伙伴找到他们时,他们正被风刮得紧贴在一道悬崖上,就在我们营地下游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他们的头领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赶走,那他们绝对是死定了。埃弥尔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他们把马拴在树上以便过夜,然后悄悄聚在一起。他们坐了下来,开始吃从系在马鞍旁的手枪皮套中取出的干山羊肉和牦牛油。在吃东西时,他们一直把武器放在手边,还不时停下来倾听细微的响动。他们随意交谈着,做着许多手势。贾斯特告诉我们说:他们对我们的设备和那个光感到惊讶。他们在寻思为什么风不刮了,为什么在这个圈子里是暖和的,还有为什么那些马这么快活。
他们中那个几乎一直在讲话的人曾听说过我们的大师朋友。他对他的同伴们说这些人就像神一样,可以随意在顷刻间把他们这些强盗都消灭。很多强盗认为我们是阴谋要抓捕他们,于是试图说服其他人把我们的东西抢光,然后跑掉。但他们的头领坚持不让他们粗暴对待我们,说如果他们对我们不好,那他们全都会被歼灭。
在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半天之后,有八个强盗站起来走近我们,对贾斯特说他们不想再留在这儿了。他们太害怕了,想试着回到自己几公里外、位于河流下游的营地中去。他们借助我们营地的树丛,总算辨认出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骑上马,开始沿山谷向下走去。但二十多分钟后,他们又都回来了,说雪太厚了,以致他们的马无法再往前走。他们自己也无法面对这场多年来最猛烈的风暴。然后他们便收拾东西准备过夜了。
我们中的一人说:“唉,虽然害怕,可我还是觉得待在这儿比待在外面的风暴中舒服。”
贾斯特转向我们说道:“天父的家就在你们逗留之处。只要你们在这个家里,只要你们住在这里,你们就置身于天父之灵的欢乐中了。但假如你们不在这个家里,或假如你们感受不到这个家里的温暖与舒适,那这里满满的温暖与舒适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可以任意邀请外面的人来,但他们不会进来,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的居所。即使感受到了这种温暖,那些亲爱的人也不愿靠近,因为他们以前经历的一直都是劫掠。他们无法理解,那些被他们理所当然视为猎物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友好地接待他们,而且那些人和他们又不是同一个团伙的。他们不知道在大雪、寒冷或最可怕的风暴中央,住着天父。无论是暴雨、狂风还是大潮大浪,都不能伤害那些以天父之家为家的人。只有当我们与上帝失去联系时,我们才会被风浪吞没。也只有当我们的双眼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凝视上帝而此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见时,上帝才能实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我目前就是这样想的:‘哦,我的天父,我坚定地凝视着你。我只感受到你。我只看见一切事物中的上帝。我稳稳地站在圣山上,只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生命和你的智慧。你的圣灵一直浸润着我。祂居于我之内和我之外。天父,我知道这圣灵不是只给我一人的,而是给你所有孩子们的。我知道我所拥有的一点儿不比他们多。我知道唯有上帝是为所有人而存在的。哦,我的天父,我感谢你。’
“人可以在风暴中央找到真正的平和,因为真正的平静就存在于那发现了其真我的人的心底。与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处于荒凉僻静之地,独自面对着暮色黄昏和大自然的无边寂静,同时却又被激情的风暴撕扯着或被恐惧的雷鸣摇撼着。
“在一个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大自然无疑更偏爱那些具有蛮力的生灵——它们粗暴、贪婪,有能力杀害弱者。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往往不被人注意的简单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羔羊比狮子多,而这并非偶然。大自然不会盲目地犯错。大自然就是工作着的上帝,而上帝不会浪费材料,也不会在建造的过程中糊里糊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在大自然那蛮力较量的熔炉中,狮子没有在人类登场前把羔羊全都吃光,反而是羔羊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彻底打败了狮子?人类对羔羊的支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结果。从各种可能性来看,人类正是通过屠杀最温和的动物来开始其血腥生涯的。人杀死的羔羊肯定比狮子杀死的多。恰恰是大自然而不是人类,宣告了对狮族的判决。
“你们好好想一想就会看出,大自然不会出于两个相反的目的而赋予同一动物以某种特有的力量。狮子是强大的斗士,却是蹩脚的繁殖者。它那精致、发达的身体里的全部力量都是用来战斗的。幼崽的出生对它来说是不利的,只是它生命中的一件小事而已。与之相反,羔羊不是斗士,因此它在身体上处于劣势。它不把能量消耗在打斗上,所以是更好的繁殖者。大自然承认她创造狮子是犯了个错,而她在纠正这个错误。狮子和所有其它食肉动物都正在消失当中。
“大自然的永恒法则对一切残暴动物宣告的这个死亡判决是没有例外的。大自然按照一个永恒的正义运作着。根据宇宙的最高法则,攻击者事先就已战败。从前一直都是这样,将来也一直都是这样,无论对动物来说还是对人来说,无论在森林中还是在城市中,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狮子已经输了。就在它赢的时候它已经输了。就在它杀害生灵时它已经开始死去。连事物的常理都要求:当狮子从羊群中夺走一只羔羊并撕碎其温热的肉体时,它得吞噬自己的种族。当第一头狮子把它的巨掌按在猎物上并用血淋淋的嘴唇发出心满意足的叫声时,它不是在给它所吞食的弱小生灵唱挽歌,而是在给它自己的种族唱丧曲。野蛮不是集群联合的征兆。狮子和熊都不成群结伙地生活。人类中的野蛮人组成自相残杀的小团伙。他们的野蛮粗暴转而对抗自己的种群并变成了他们衰弱的根源。
“以此类推,野蛮人的团伙也定会消失。任何一个强大的斗士都从未真正赢得过什么。一切胜利都是虚幻的。当那些军事帝国除了利剑之外别无所依时,它们就会迅速土崩瓦解。到了最后,那些领导者必得放弃武力并求助于正义和理性,否则就得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帝国崩溃。人类或动物中的残暴者都是孤单寂寞的,没有希望、孤立无援、罪责难逃,因为柔和是唯一真实的力量。柔和,那就是一只狮子从其所有品性中减去嗜血的习性。柔和会慢慢让一切生命都服从于它那终将获胜的法则。
“人可以自我成就,也可以自我毁灭。在思想工厂里,人可以打造出用来毁掉自己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出用来为自己建造欢乐、持久、平和的天堂居所的工具。通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良好选择和正确运用,人能够达到神圣完美的境地。而通过滥用和错误使用思想,人也会跌落到比野兽还低的地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呈现出各种各样有着细微差异的性格层级。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也是自己的主人。
“这儿的这些人是一个曾经伟大、繁荣的民族的残余。他们的祖先居住在这个地区时,这里是一个兴盛、美好的工业帝国。他们从事科学和艺术活动。他们也了解自己的起源和力量,并且只崇拜这个起源和力量。到了某个时候,他们开始从肉体上获取享乐。但肉体很快令他们失望了。这时一场大洪水毁掉了这个国家,只留下一些与世隔绝的山区居民。这些残留的人聚集成群体,从中产生出了那些大的欧洲种族。
“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地区以及戈壁沙漠地区,那时被切割开来并被抬高到了一个寸草不生的海拔高度。这些地区的居民几乎被彻底消灭,只留下了极少数孤立的群体,有的甚至只剩下一、两户人家。这些群体聚集成了团伙。那就是这些人的祖先。他们不可能兴旺发达起来,因为他们相互间总在不停地争斗。他们的历史和起源已被遗忘了,但他们的宗教和传说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其基础都是相似的,只是形式上有很大差异。”
这时贾斯特说他恐怕让我们听得厌倦了,因为我们大多数朋友都已经睡熟。我们朝那些强盗望去——他们都睡着了,和我们一样已忘记了那仍在肆虐的风暴。我们回到自己帐篷里,再次向大师朋友表示感谢后便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阳光灿烂,整个营地都活跃了起来。我们急忙穿好衣服,发现所有人——包括那些强盗——都在等着吃早饭。我们吃饭时,有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天的日程安排,那就是陪同这些强盗直到他们的营地。的确,大家一起走要比分头出发更容易开辟道路。这个计划让强盗们很高兴,却不怎么让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得知在他们营地那儿有一百五十人。
我们吃完点心时,残余的风暴也已消失。于是我们拔营而起,和强盗们以及他们的马匹一同出发去开辟道路,委托其他人带着野营用具跟在后面。
强盗们的营地在下游不到二十公里处。但我们直到下午才抵达那里,非常高兴能在那儿歇歇脚。我们发现这个营地很舒适,地方也足够宽阔,可以容纳我们整个考察队。吃过午饭后,我们看出最好在当地待一到两天,等雪化掉些再走,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本来我们第二天就得去翻越一个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但天气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暖和起来,于是我们把逗留的时间延长到了四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对我们极其尊敬,并尽一切可能让我们感到舒适愉快。
在我们出发时,有两个男人来问是否可以加入我们的考察队。我们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们反正也得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下一个大村子里招收一定数量的助手。这两个男人就一直陪同我们,直到我们秋天返回这里。
当我们离开这村子时,村里近一半的人一直把我们送到山口上,好帮我们在厚厚的雪中开辟道路。我们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盛情,因为登山的过程实在很艰难。在山顶上,我们告别了这些强盗朋友,然后朝约定地点走去。我们于5月28日到达了那里,比按照去年秋天的约定去那里与我们会面的那些分队的朋友晚到了三天。
【相关阅读】
- 【大师们的生活】(29)《接收神圣思想的脑细胞及活动人像》
- 【大师们的生活】(28)《 听耶稣谈地狱、上帝与基督》
- 【大师们的生活】(27)《一位灵修者的复活与扬升》
- 【大师们的生活】(26)《祈祷方式与灵性声像术》
- 【大师们的生活】(25)《在“T”字形寺见到耶稣并听其教诲》
- 【大师们的生活】(24)《“第七重天”的存有在除夕之夜的教导》
- 【大师们的生活】(23)《喜马拉雅山中的大师聚居地》
- 【大师们的生活】(22)《大师谈人类合一及灵性成长》
- 【大师们的生活】(21)《天使在盛宴上的智慧教导》
- 【大师们的生活】(20)《来自外星球的大师之母》
- 【大师们的生活】(19)《与《圣经》惊人相似的印度古文献》
- 【大师们的生活】(18)《失重感及与一位女性大师的会面》
- 【大师们的生活】(17)《雾中的奇光与幽灵》
- 【大师们的生活】(16)《大师们的外表及瞬间消除疲劳》
- 【大师们的生活】(15)《一位永生不死者的教诲》
- 【大师们的生活】(14)《施洗约翰的行迹及神奇疗愈》
- 【大师们的生活】(13)《山巅古寺及避火术》
- 【大师们的生活】(12)《远程交流及雪山野人》
- 【大师们的生活】(11)《宇宙能源及第七重天》
- 【大师们的生活】(10)《宇宙思想及美国的灵性作用》
- 【大师们的生活】(9)《疗愈之寺》
- 【大师们的生活】(8)《水上行走》
- 【大师们的生活】(7)《创造一切所需》
- 【大师们的生活】(6)《静默寺的启示》
- 【大师们的生活】(5)《青春永驻的奥秘》
- 【大师们的生活】(4)《神奇的分身术》
- 【大师们的生活】(3)《身体的消失与重现》
- 【大师们的生活】(2)《大师在圣诞节的教导》
- 【大师们的生活】(1)《与一位印度大师的初次接触》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